河合隼雄:霸凌在大人看不见的地方发生,不只是“弱肉强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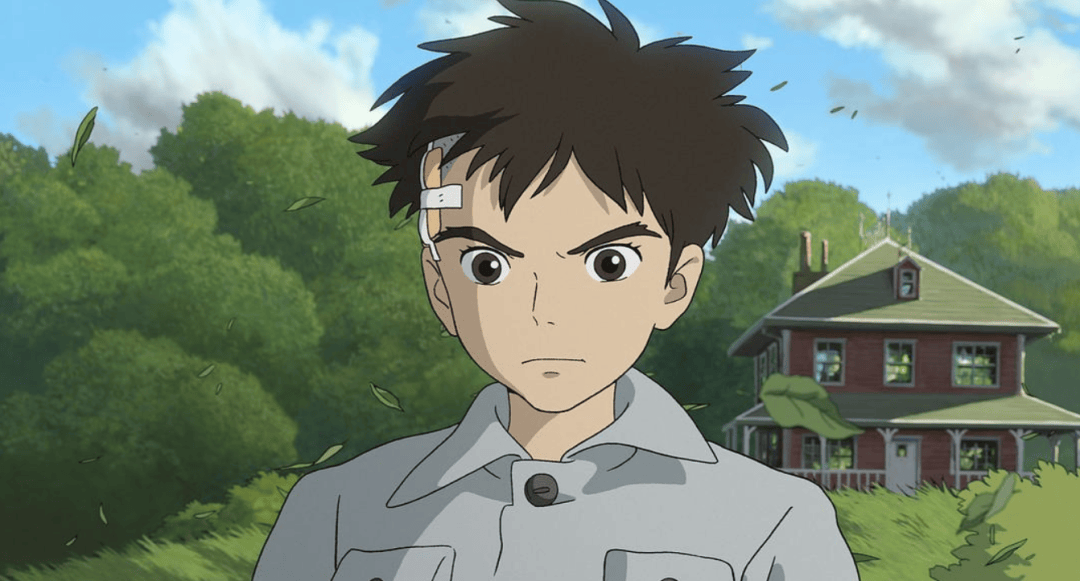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剧照。
关于霸凌的探讨,从未停止。很多人觉得孩子被霸凌,是因为本身不够“强”,但对于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和哲学家赤坂宪雄来说,这种弱肉强食的思维与青少年所处的现实有所偏差,成人更难以窥见霸凌的真相。
在以下对谈中,河合隼雄和赤坂宪雄认为,霸凌表面上是欺负与被欺负的对峙,实际上则是由“猜测和偏见”引发的冲突。在群体中,霸凌往往并非由一个人完成,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某种难以置信的原因成为“异人”,进而被群体霸凌。

河合隼雄(1928-2007),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日本第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曾任日本文化厅厅长、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著有《心的栖止木》《大人的友情》《爱哭鬼小隼》《孩子的宇宙》等。
同时,对“好孩子”的单一定义促成了霸凌的加剧,单一的评价标准下,将他人“异人”化的行为会更频繁,也有更多名目。当谈到如何在观念中消解霸凌时,河合隼雄说:“如果大家能认识到人本来是千姿百态的,哪怕只是父母和教师认识到人多样化的美,也会有很大帮助。”
作者|[日]河合隼雄 [日]赤坂宪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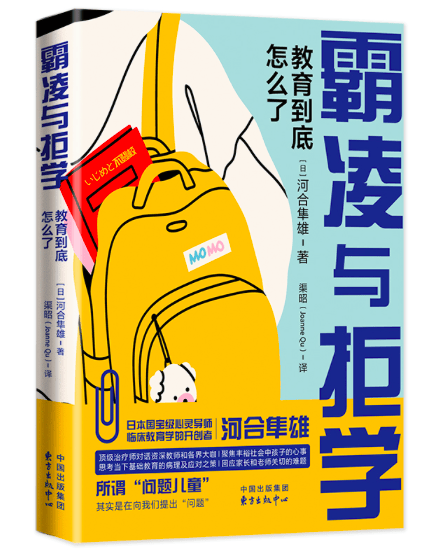
作者: [日]河合隼雄,译者: 渠昭,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时间: 2024年2月
小小课外辅导班里所见的“霸凌”
河合:我们在临床教育第一线工作,霸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赤坂先生是一位哲学家,您对这个问题也一定非常有兴趣。我想先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的起因,以及这个问题在您的研究课题中的意义。
赤坂:我从二十大几开始,大概有十年时间曾在课外辅导培训学校当教师。那是一个只有附近孩子参加的每个班只有三四个学生的小型辅导培训学校。
河合:大约是什么年龄的孩子?
赤坂:多数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高中左右的学生。我当然没有特别挑选过,不过来的都是些在学校受欺负的、拒绝上学的、态度一贯恶劣的孩子。好像去不了大辅导培训班的孩子们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从现在算大概是七八年以前吧,我比较有机会听得到这些孩子嘟嘟囔囔。
我是比较早就开始注意到“霸凌”问题的,差不多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吧。我就是那时候开始注意到,学生中有人用“村八”或“八分”这些词的。我纳闷他们在说什么,再仔细听,他们说的是“村八分”(“村八分”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村落中实行的一种民间惯例,是在一个村子里,全村对不遵守村规的人家绝交的制裁行为。有“废除”“排斥”“被大家排挤在外”的意思。——译者注)。这就是我遇到的这些根本不可能懂“村八分”含义的孩子,却口口声声“八分”“村八分”地欺负谩骂同学的最初一幕。所以应该说,因为觉得学生的这个说法奇怪,我才开始注意到了学生中的霸凌问题。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被欺负对象不断地变化这一点。在我非常惊讶时,正好有人受欺负了,所以我就去问当时七八个人的一个小组里最聪明,运动方面又好,又关心他人的少年。我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就这么一句话,欺负人的动作竟忽然消失了。我想这应该是我问了以后的结果。

《孩子的宇宙》,作者:[日]河合隼雄,译者: 王俊,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时间: 2010年1月
河合:应该是这样的。
赤坂:那时候没什么经验,以为说一句“别那么卑鄙地欺负别人”就能制止这种事。那次的事突然消失后不久,接下来那个爱关照别人的孩子就开始受欺负了。他变得非常忧郁,我当时对此事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也就是说,团体里蛮有威信的这个小头头,按常规不会受欺负的少年却也在被欺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感觉到事情的奇怪,到发现了今天的霸凌跟我们小时候的被欺负不同。这样,我便开始注意霸凌问题了。
河合:因为你在校外辅导培训班工作,所以能看到霸凌的情况,这一点我很理解。另外,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的霸凌与过去的欺负人并不是一回事。这样的人会说,欺负人的事,不是早就司空见惯了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认为霸凌是一句话就能控制的事情。这样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直接造成了霸凌问题日益增多的局面。而且,连以前不可能受欺负的人,现在也成了被霸凌的对象。
赤坂:而且,霸凌的概念和性质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比如说以前还没上学的孩子,只要三四个人在一起,也必然会出现欺负人的事情。但常见的欺负人的情景是,比较强壮的孩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去攻击软弱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强壮的孩子对付几个软弱孩子的情景居多。可今天的霸凌现象则不然,被欺负的对象往往是一个人,欺负人的却占多数,有时甚至为整个团体。这种情况与“故意冷落别人”及“村八分”的说法相关联。当我们能从表面上清楚地看出这些特点时,就知道这种霸凌的性质与之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
河合:如果只是弱肉强食的问题就比较容易明白,可今天的霸凌并不是这种情况。现在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霸凌方式也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对赤坂先生来说,您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并从这方面进一步探索和理解人性问题。
然而,家长和教师其实很难看到霸凌,对此怎么才能说清楚呢?当然孩子们偷偷摸摸地欺负人也是事实,大人真的看不见。正如一开始您曾提到,课外辅导老师与学生们在一般交往中可以看到一些,可当你想去干涉一下时,霸凌会立即消失。之前他们也许会把辅导老师当成朋友,你若想引导一下,他们会马上意识到“那家伙是大人”,对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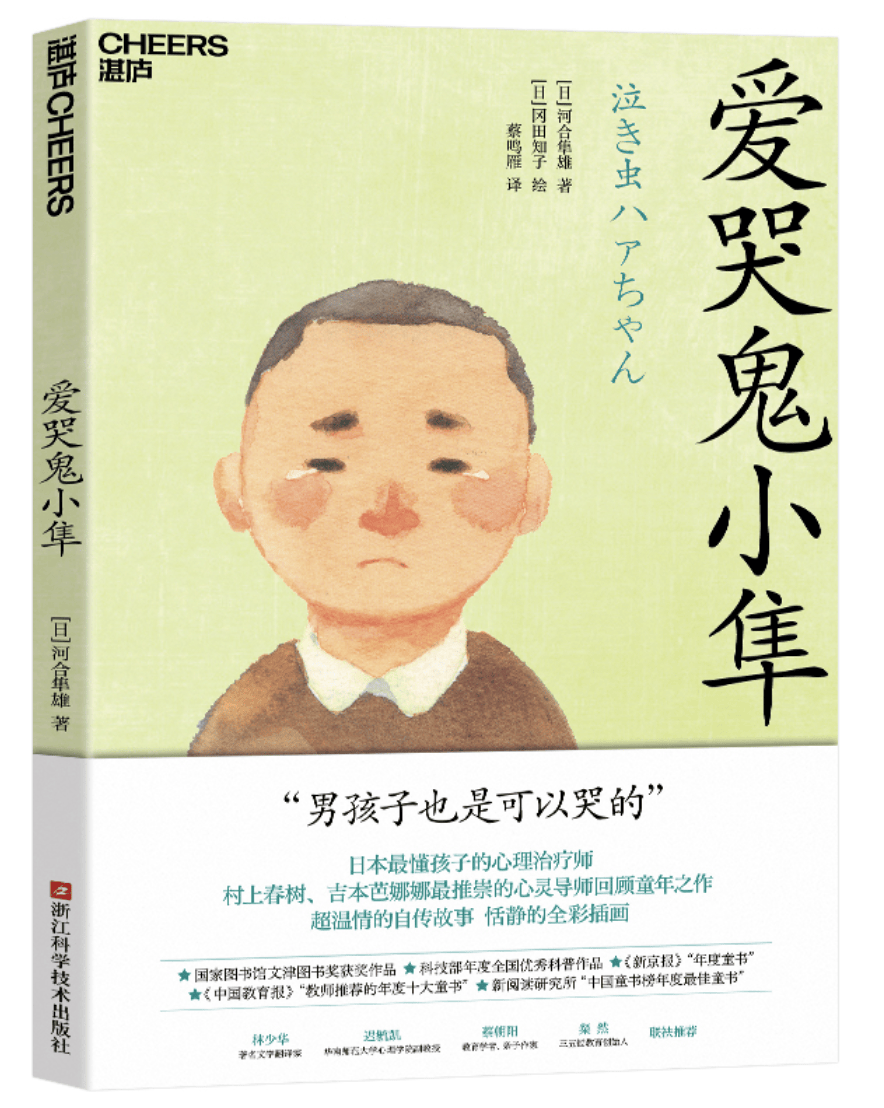
《爱哭鬼小隼》,作者:[日]河合隼雄 著 /[日]冈田知子 绘,译者: 蔡鸣雁,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3年1月
赤坂:对。所以我只管了一次即以失败告终了。之后,便采取不直接干预而进行观察的态度。这样,孩子们就会小声说一些欺负人和被人欺负的事。
比如,有一次,听到两个像是初中三年级的女学生在说一件事。原来是说班上有个不顺眼的学生,遭到了很厉害的欺负,现在不来上学了,结果住进了精神病院。作为肇事者的这两个女学生竟然说,“她现在住院了,那咱们今天晚上拿一把花追到医院去看她”。我从这里看到了非常残酷的一幕。
还有,一个像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被人起外号叫沙袋,受严重欺负,遭拳打脚踢。他来跟我说这件事,却不说自己被欺负了。他说“老师,我班上有一个孩子被人起了‘沙袋’的外号,遭到了欺负”,反反复复说了好多次。我后来才发现他说的原来是他自己。
他这样反复跟我说这件事,其实并不是期待我出面帮助解决问题,而只是为了找到一点安慰。那时候我一直比较注意听这些情况。不过后来自己工作过忙,就顾不上了,孩子们也不再来跟我说了,以至于后来完全听不到了。之后,我虽然辞去了校外辅导培训教师的工作,当时的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体验。这些体验让我有机会,从一个辅导培训班教师的角度对霸凌有了一些观察。
从受尊敬到被排除的转校生
赤坂:从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我碰巧在做有关异人(stranger)方面的研究。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课题是,从一个团体里被排除出来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有什么属性,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我将霸凌问题的研究看成异人论延长线上的研究。
河合:请您就异人论的研究向大家作一些说明。
赤坂:传统上对异人有“流浪及定居双重性格”的定义。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团体具有自己的秩序,就有可能存在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的人。或当一个与这个团体持有不同行为准则的“来访者”来访时,则会产生各种摩擦。我是从异人论的观点出发,来讨论这些现象的。
霸凌问题在表面上是欺负与被欺负对峙的情景,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孩子们之间小规模的摩擦。它象征性地表现了一个团体或一种秩序所处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霸凌问题是由种种猜测和偏见引起的。我在自己的研究里曾把异人分成若干类。在这些类比中,我总感觉霸凌问题似乎与边缘人(marginal man)相关。
河合:说到异人,与霸凌恰恰相反。如在民间传说中经常见到“稀客”来访的故事,比如弘法大师来访那样的故事。这类故事多具有正面意义。但今天的霸凌却只有负面作用。常常是整个团体一同开足马力去排除这个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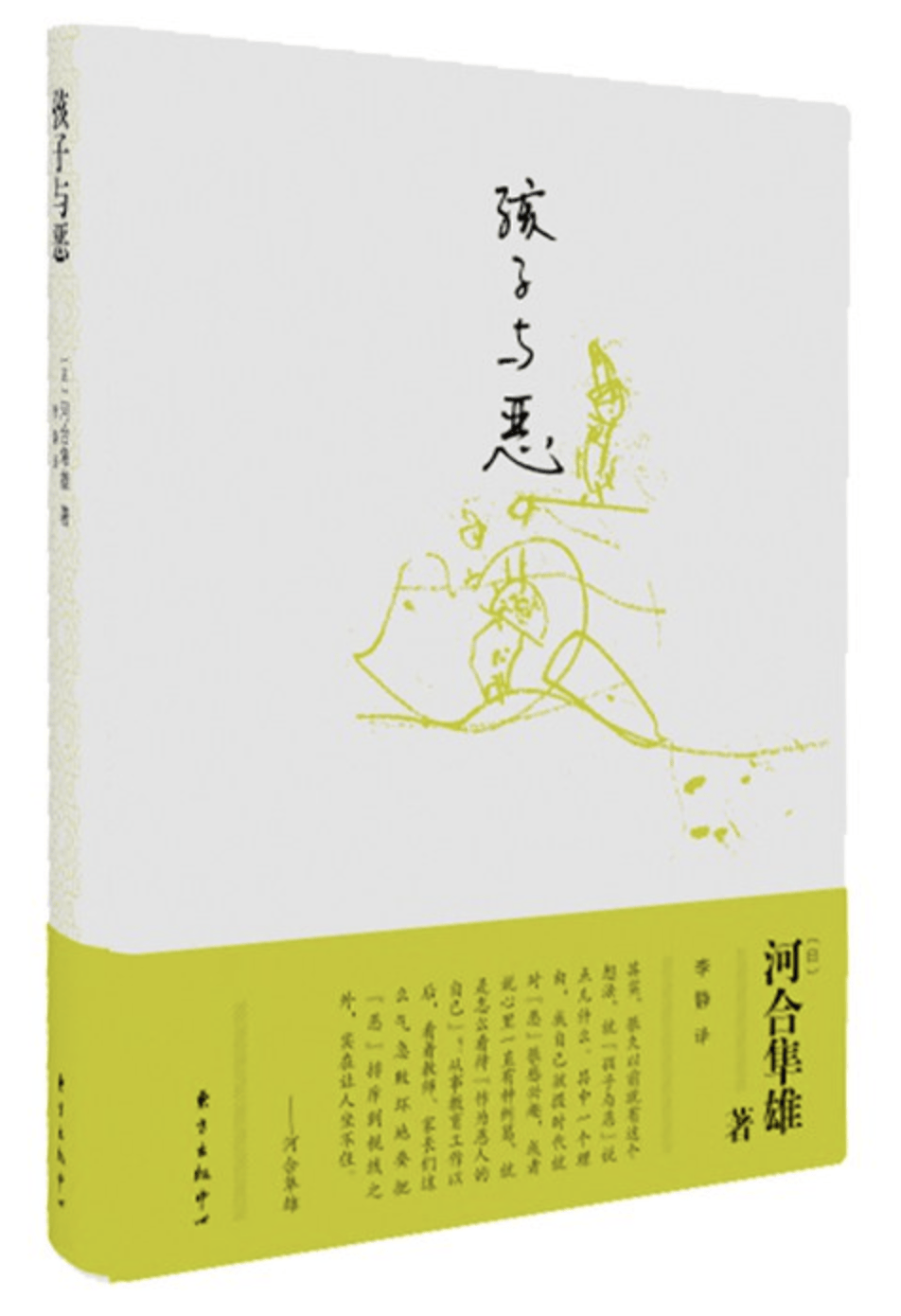
《孩子与恶》,作者: [日]河合隼雄,译者: 李静,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时间: 2015年4月
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虽然受欺负的孩子被视为异人,但他们其实并非异人,而原本是团体中的一员。所以,他们受欺负的原因并非在于新来乍到,而是本来属于这个团体中的人突然遭到了欺负。
赤坂: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重要。我们观察民间故事里通过“外来客”所表现的信仰就可以发现,他们看上去像乞丐一样肮脏,实际上同时具有弘法大师那样神圣性的双重性格。所以,其中存在着一种相互矛盾的构造原理。比如不招待乞丐就要遭报应,畏惧和敬仰往往兼而有之重叠在一起出现。可在现代,至少在霸凌现象中并非如此。
我对转校生问题很有兴趣,不知在这里是否能成为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
河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转校生是异人。
赤坂:在少年少女漫画中,转校生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比较多的时候,转校生在漫画故事的世界里会起着拯救团体,或是引领这个团体走向某个新方向那样的积极作用。所以,他们经常会成为故事的主角。比如《明日之丈》(或译作《小拳王》)的少年主人公,很显然是个突然从外地流浪而来的孩子。后来,因为干了坏事被送进少年犯管教所。在少年犯管教所里,他接触到了拳击,最后登上了世界拳坛顶峰。虽然他的出身、来历被写得比较暧昧,可在当今枯燥的学校环境里,类似这种乌鸦变凤凰的事情已经很少见了。
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转校生还会像《风之又三郎》里所描写的那样,带有很强的异国情调,大家会围过去问东问西,互送礼物,然后互相渐渐熟悉起来。那时候转校生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同时也会被欺负。
河合:正如你刚才说的,他们具有两重性。
赤坂:可是,现在的转校生很难像从前那样,顺利地被团体接受。

《童话心理学》,作者: [日]河合隼雄,译者: 赵仲明,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时间: 2015年5月
河合:的确很难。转校生多数要遭到欺负。特别是海外归国人员的子女,会受到特别恶劣的欺负。其中也有人顺利融入新团体,并受大家喜爱,但为数极少。
比如,从海外回来的孩子当然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这样老师就不开心,因为老师说的是日本式的英语。孩子漂亮的英语一出口,就让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我说的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老师对孩子说“我们这儿是教日本英语的地方”(笑),结果这孩子彻底变成了被霸凌的对象。
也就是说,老师的一句话就使一边形成一个日式英语集团,而归国人员子女这边则被大家嘲笑,被起上“怪日本人”的外号。如果换一种方式,比如老师说“你的发音真好,大家应该模仿这位同学的发音”的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剧照。
赤坂:我在自己的“异人论”研究里,把异人分为六种类型。第一种是在集团边缘擦边而过的流浪人,第二种是从其他集团过来的来访者,第三种是暂时的逗留者,第四种是被排挤到集团边缘地区的边缘人,第五种是回乡者,第六种是蛮人,这类人被视为野蛮人,常遭到非常严重的歧视。
我认为回乡者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现在海外归国人员子女问题来说,具有双语能力及多种语言能力,这成为他们受欺负的主要原因。
河合:一不小心打破这些分类,就有可能把所有的人都一起并入蛮人一类。不做选择分类,而一股脑地认为“那个做法奇怪”“这家伙不行”,来势汹汹。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均一化与寻求差异
河合:刚才说起可以把异人分为几类,如果人们心中对周围的人有类似的区分观念,那么即使是比较怪异的、滑稽的或较软弱的孩子,也会得到相应的评价和认可。现在人们心里的这种区分却正在消失,这是霸凌方面的一大问题。
赤坂:您认为这种区分真的消失了吗?
河合:是的。在我看来,我们对“好孩子”的定义太单一了。如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孩子,那么也就可以允许有各种类型的“坏孩子”。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明确认为只要会学习,成绩好就是好孩子。这样,就很难接受其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各种类型的孩子。
赤坂:我隐约感觉到,均一化的观点对不同存在非常缺乏宽容性。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的学校是一个受到高度均一化管理的团体,完全失去了与不同存在交流的场所和渠道。同学之间即使是微小的区别,也能被视作天壤之别。我感觉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出现那种把一些本来只有微小区别的人,硬变成了整个团体不能容忍的蛮人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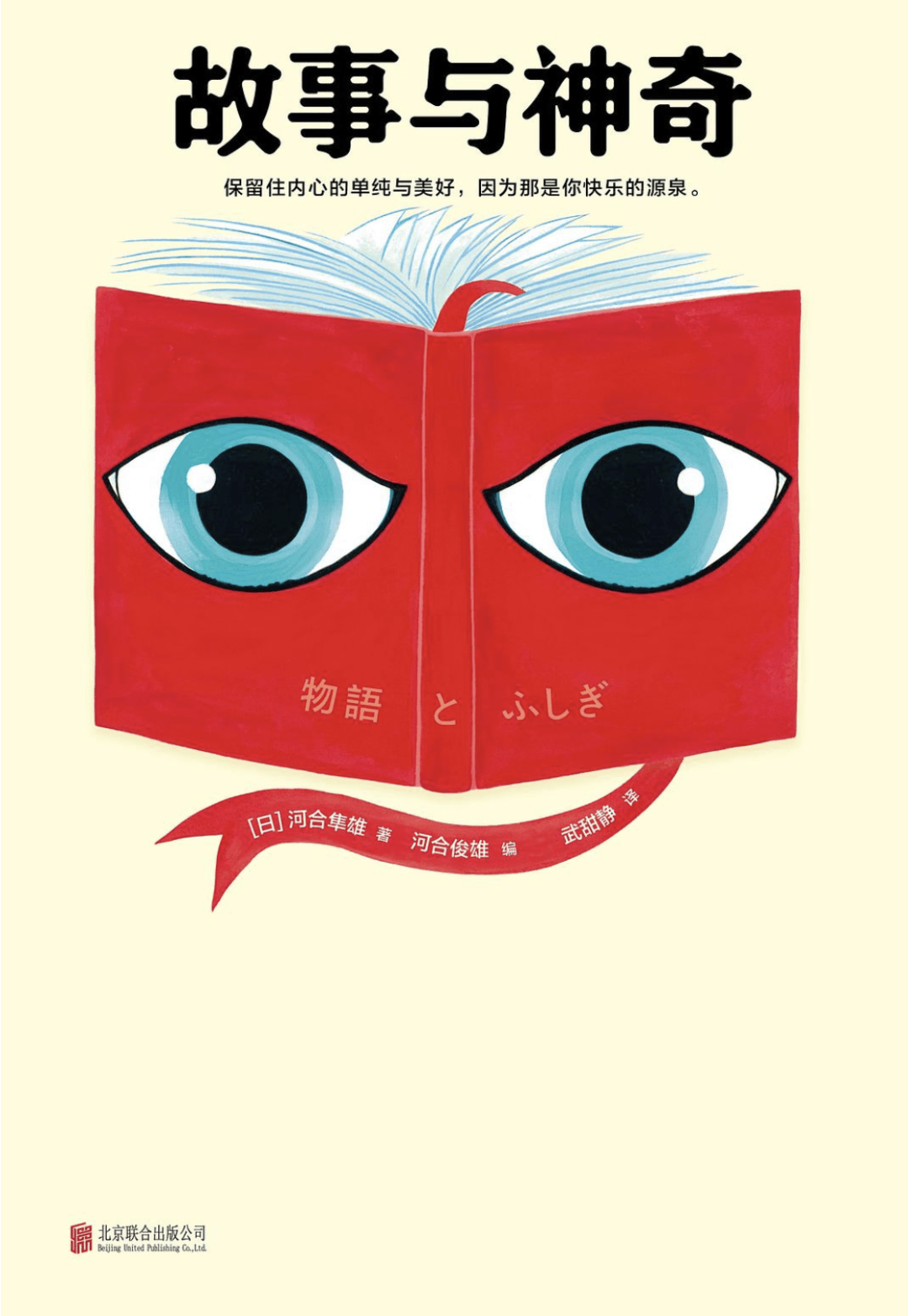
《故事与神奇》,作者: [日] 河合隼雄 [日]河合俊雄,译者: 武甜静,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 2018年8月
河合:由于均一化是强迫形成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承受巨大压力。本来每个人应该是不同的,可是全被压制成同等均一的了。因此,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怨气。这时候,如果团体内冒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则会千夫所指。
赤坂:是啊,周围会出现不可想象的巨大敌意。比如,如果大家没在看同一部电视剧,聊天就持续不下去那种情况。为什么大家得绝对一致呢,被迫感实在太强烈了。
河合:大家做着同样的事情,心里却一直都有一些不满和无奈。憋屈在内的那股气要发出来时,就得有一个人承受下来。刚才提到了异人的分类,如果大家能认识到人本来是千姿百态的,哪怕只是父母和教师认识到人多样化的美,也会有很大帮助。这方面太欠缺了。现在说到好孩子,清清楚楚的只有一种模式而已。
赤坂:恶果是即使是教科书般的好孩子,有时也会突然一变,而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河合:成绩太好也会引起别人不满。本来完全不会成为被欺负对象的孩子,也会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发生逆转。

《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剧照。
赤坂:物极必反,过犹不及。
河合:比如,模仿好学生说话腔调那样的调侃行为。
赤坂:当隔着一定距离观察孩子们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集体中太孤僻的孩子会受欺负,太阳光的孩子,过于引人注目了也会受欺负。孩子们得一边细心环顾周围,一边不断调整其间的平衡,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偏差值调节在五十上下。现在的孩子们都这么磨炼着自己的处事方法。如果对这些能看开一些,勇敢面对,自己就会轻松很多。
河合:我认为刚才提到的这些,实际上是现代霸凌问题的本质。当这些现象的底流部分与青春期问题重叠时,便会引起强烈震动。
原文作者/[日]河合隼雄
编辑/王铭博
导语校对/卢茜
事情 地方 变化 大人版权声明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